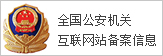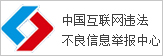□ 崔正升
“减负”不仅是当今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,也曾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中的重要议题。清末以降,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,肩负着开通民智、塑造国民精神的国文教育被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。这不仅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现代转型,也为教育“减负”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一、废八股。科举考试本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,它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,给寒门学子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。但是“法久弊深”,明清两季的科考以八股文为主,要求内容不许超出《四书》《五经》范围,考生还要模仿圣贤口气“代圣贤立言”。这种僵化的考试不仅泯灭考生个性、抑止学习兴趣,而且竞争激烈,淘汰率极高,无形中加重了考生的心理、学业负担。清华校歌的词作者汪鸾翔在《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》(1920)中回忆道:“彼时不但四书五经,全要背诵,就连朱子的注解,也都全要背咧。一个幼弱的脑筋,要容纳许多的古物,也算是力小任重的了。”而考生为了作好八股文,还得将《八铭塾钞》《韫山文稿》《赋学正鹄》《试贴七家诗》等艰涩范文“横七竖八地装上他一肚子”。但是古代读书人出路很窄,加上考中后会有丰厚的物质名望回报,从而诱使考生将一生精力投入科场,造成了惊人的人力资源浪费。
鸦片战争后,面对日渐衰颓的国势,一批有识之士将变革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出路,废科举、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。晚清改良主义先驱冯桂芬在《改科举议》(1861)中指出,八股取士“所取非所用”,并且考生“一科复一科,转瞬而其人已老”。梁启超在《论科举》(1896)中也指出考生“尽数十寒暑,疲精敝神以从事于此间”,“故欲兴学校、养人才以强国,惟变科举为第一义”。显然,这都是从实用、减负的角度考虑的。直到1905年,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,才不得不下令“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”,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总算废除,八股文也宣告寿终正寝。当然,废除科举并非万全之策,但它毕竟催生了新式教育的发展,改变了以往学生皓首穷经的苦熬心理和“惟科举是务”的成长路向,尤其是“废八股”在客观上解除了学生的思想枷锁,降低了考试难度,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业、心理负担。
二、禁读经。从本质上说,清政府废止科举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,带有鲜明的改良、变通色彩。张百熙、荣庆、张之洞在《走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》(1903)中就指出:“然则并非废罢科举,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。”可见他们主张废止的是科举制度的形式,而非内容。由他们拟定的《学务纲要》(1903)规定“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”,认为“惟童子正在幼年,仍以圣经根柢为主,万不准减少读经讲经”。1903年颁布的中小学《奏定学堂章程》都设有“读经讲经”科,并且每周的“钟点”数都远多于其他科目。事实上,当时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没摆脱“讲经读经”“讲古文、写文言”的局面,语文学科作为经学附庸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。1912年1月,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,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提出“实利主义”等“五育”并举的教育方针和“尚自然”“展个性”的儿童教育观,其中之一便是废止师范、中学、小学读经。但袁世凯复辟后又规定“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”,不过随其迅速垮台读经活动也不了了之。1916年10月,教育部公布了修正的《国民学校令》与《高等小学校令》,明确删除了“读经”课及有关内容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局势、争取民心,实施“尊孔读经”的文化复兴政策,蒋介石、何键、陈济棠等政治人物亲自上阵,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尊孔读经运动。与此同时,为压制国人反抗思想,东北伪满政权也大肆推行以读经为主的奴化教育。由于各股势力鼓吹读经的目的不尽相同,文化教育界曾于1934年以《教育杂志》为阵地,对中小学要不要读经展开了激烈争论。结果多数人反对中小学读经,理由是经书语义艰深,其思想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,会加重学生课业负担。如傅斯年在《论学校读经》(1935)中就指出,“现在中小学的儿童,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,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,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”,何况“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以安排,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,又怎样办”?后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,中小学读经运动逐渐平息,此后再也没有掀起大的风浪。读经曾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途径,在传承文化、塑造人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经书的文字艰深晦涩,内容多偏于道德教化,加之教育方式机械灌输有违认知规律,令学生枯燥乏味、苦不堪言。民国废除中小学读经有力冲击了传统灌输式教育,在尊重教育规律,减轻课业负担,顺应学生身心发展方面意义深远。
三、倡国语。我国教育在清末时期十分落后,文盲、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%以上,国民大多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,多数人用的是方言。而当时主导书面语的却是与口语严重脱节的文言文,学习起来费时耗力,加之方言的地区差异,这给普及教育、日常交流带来很大不便。在开启民智、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潮中,清末兴起了以实现“言文一致、统一国语”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运动,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。首先是始于清末的白话文运动,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向高潮,直接促成教育部于1920年1月训令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。这道训令被看作语文教育现代变革的重要标志,白话文在教育制度层面获得合法身份,胡适称其把中国教育革新“至少提早了20年”;黎锦熙则盛赞该举措是“救济儿童”“解放儿童”。自此以后,白话文打破了文言一统语文教学天下的局面,学生的阅读和写作都逐步改为白话文,不仅极大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程度,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学习语文的门槛,大幅减轻了学生负担,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。
其次是切音、简字、注音字母、文字改革等国语运动。汉字是表意的文字,字数多、笔画繁、读音乱、检索难,成为困扰汉文学习者的首要难题,这也无形中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。如何使汉字更适合于人们的拼写、学习和交流,清末以前人们就在思索和尝试汉字改革的问题。而真正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,不论是较早的切音字运动、简字运动,还是民初的注音字母运动,以及后来罗马字运动、汉字拉丁化运动等,都极大方便了汉字的书写和使用,有力推动了汉语的教育和普及。
再次,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变更书写款式也成为语文变革、教育减负的重要举措。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没有标点符号,读者要靠自己的理解来断句,这不但影响了阅读效率,也徒增了负担。1896年,王炳耀在《拼音字谱》中创制出十种标点符号,成为我国第一个新式标点符号系统。1919年4月,由胡适起草,他和周作人、朱希祖、刘复、钱玄同、马裕藻共同署名的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》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通过,后经教育部公布实施。我们今天所用的标点符号就是以此为蓝本,不断修订完善而成的。还有,书写款式由“右起直行”改为“左起横行”。清末推行“切音字”时期,个别拼音读物曾尝试“左起横行”,而1915年创刊的《科学》杂志已采用横行书写。1917年5月,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上与陈独秀讨论西文译名时提出“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”的主张,理由是横视“甚为省力”,纵视“颇为费力”。1918年8月,朱我农在《新青年》上也撰文指出“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,又可以安放句读符号”。后来钱玄同在与陈大齐讨论该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直行书写须“悬腕”,以防墨迹印在手上,而横行就可省此麻烦。可见当时倡导横行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节省目力、减负增效的角度考虑的。尽管横行书写未能形成推行白话文的声势,但这一主张却颇具远见,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,一些杂志、教科书及学生作文开始采用横行款式。
综上所述,清末民国时期几项国文教育变革措施均体现出了“减负提效”的现实诉求,它将众多学子从过去皓首穷经的枯燥生活中解脱了出来,让语文学习变得容易、轻松了许多。这些改革举措既受近代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影响,也深受“五四”科学教育思潮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、儿童中心教育思想的启发,而其成效则离不开官方法令制度的推行与保障。这也启示我们,学生减负一方面要践行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教育理念,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,另一方面要在系统化的制度设计、法令保障方面做足文章,真正做到学生减负与提质增效两手硬、两不误。
(作者系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、中国写作学会理事、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在读博士)
版权声明
1.本文为甘肃经济日报原创作品。
2.所有原创作品,包括但不限于图片、文字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、信息等,未经著作权人合法授权,禁止一切形式的下载、转载使用或者建立镜像。违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
3.甘肃经济日报对外版权工作统一由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(甘肃云数字媒体版权保护中心有限责任公司)受理对接。如需继续使用上述相关内容,请致电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,联系电话:0931-8159799。
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